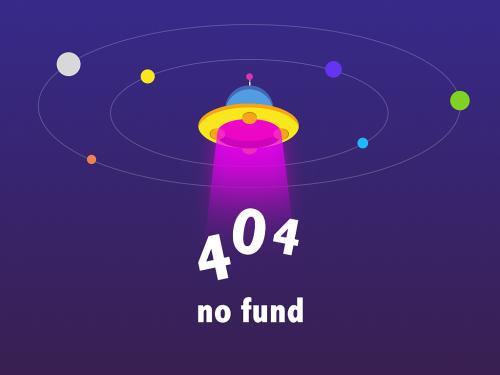□刘友洪
我的故乡紧邻大凉山麓,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,山高水长、交通不便。记得1984年秋天,我初中毕业考上中师去乐山上学时,故乡还不通汽车,是母亲帮我拿着行李,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,到邻镇才坐上长途客车。
我的小学、初中是在一个叫“牟祠堂”的地方上的,那曾是牟姓人家的宗祠,解放后改作了学校。学校在大山脚下,围墙外就是奔腾不息的大渡河。当时我望着那河水,多么渴望自己能化为一叶扁舟,去看看城市,然后奔向大海,逃离这铁桶般的大山。我的家就在学校背后的大山上,从家到学校要走十多里山路,花上一个多小时。那时我还没见过水泥路、柏油路,全乡唯一的硬化路是乡场上的石板路,每次到乡场上踩着那早已被磨得发亮且略有些凹陷的青石板,那种不溅泥点子的感觉,已让我感到很幸福。
“羊肠小道”“天晴一把刀,下雨一包糟”……这些谚语用在故乡的山路上,再贴切不过了。爬坡上坎,翻山越岭,走完那十多里山路,海拔要上升或下降500多米。如果是在雨雾天行走,还有种腾云驾雾之感。可就是这样的山路,把我童年空空如也的脑袋与学校教育、知识连在了一起。那山路穿过岁月的沧桑,至今仍能让我真实地触摸到童年的故乡。
那时,山路全是黄泥巴路,雨后路面泛着惨白的微光,我们终年走在这条路上,知道那光的杀伤力,泛光处是打滑最厉害的地方,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踩的。即使这样小心,一趟下来,浑身也会溅满稀泥,不仅裤腿两侧有厚厚一层,鞋底泥更让我连提脚都感到沉重。有次我怕上学迟到,一路小跑,在一处陡坡摔了个“狗吃屎”,还往前溜了一丈多远,手掌被磨破了皮,膝盖磨了两个洞,痛得直泛眼泪花儿。
当然,这山路也带给了我欢乐。我上学时中午是没饭吃的,熬到放学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。路过树林时,我就会拼命搜寻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。大自然是怜爱山里娃的,那时的我享受过许多现在的孩子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山珍佳味,比如刺泡儿、八月瓜、土地瓜。还有长在油茶树上的茶耳,肥肥的微红或微白的叶片,入口甜丝丝、嫩脆脆。农家地里的黄瓜、红薯等也是现成的,顺手采下一根搓一搓,连皮儿一起吃到肚子里。
故乡其实也有一条当时被称为“公路”的路,那是为勘探山中矿产而临时修建的便道。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,它连机耕道都算不上,不但窄得仅能通过一辆手扶式拖拉机,而且路面极不平整,碗口大的石头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中央,拖拉机压上去,颠得上蹿下跳,嘴里还不住地“突突突”冒着黑烟,好像随时要把它那颗“铁心脏”给吐出来似的。放学回家的我们既累又饿,满心希望能碰上这个铁疙瘩,巴不得能被它捎上一程。拖拉机来了,我们悄悄尾随,趁驾驶员叔叔不注意,双手吊在货箱挡板上。现在想来,其实他是知道的,只是他心疼我们这些读书郎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让我们轻松几步。如果遇上陡坎急弯,他就停下车来,把我们赶下车去,那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。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故乡的山路迎来了脱胎换骨,它像一条长龙盘踞在大山身上,不见首尾,只断断续续露出些身子来,然后又隐没于山谷林间,有时又像变戏法般长出些爪子来,伸进了各家各户。公路修通了,原先那些沉睡的物产也就值钱了,乡亲们过上了好生活。吃过晚饭,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公路散步,三三两两,谈天说地,其乐融融。
我由衷地感叹时代的变迁与伟大。
(作者单位:眉山市政协)